
凌力(1942年-2018年)
凌力,茅盾文学奖得主,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原北京作协副主席,因病于2018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凌力
舒晋瑜 | 采访手记
对作家凌力的采访,开始得太晚。当辗转联系上凌力时,她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以前。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晓舟热心相助,我们的采访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拖了很久;更感谢凌力,有很多回答内容,是她在病床上完成的,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写好几天,甚至屡想作罢。不论怎样艰辛,这篇采访总算完成了,这是对凌力创作的一次全面梳理,当然更包括她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想法。
时光回溯到1980年。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上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开启了凌力的历史小说创作之旅。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数次,她心安理得地坐自己的“冷板凳”,为自己留下一个虚空而静谧的心境。评论家李树声认为,这并非凌力刻意的人格自塑,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参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执着的专情。
凌力对历史的爱好,是小时候从京剧中得到的。大量的三国戏、水浒戏给她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爱文兼爱史的“病毒”,且伴随终身甚至无可救药,这使她毫不追悔地走上历史小说创作的路。京剧对历史的浓缩和概括能力,其戏剧性矛盾的发生、发展、高潮、煞尾及场次的轻重、角色的分派等等格式,细心的读者大约可以从凌力的作品中找到某些印记。
从秦汉到清末,中国的封建君主制社会不中断地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为什么?这是凌力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史学家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科学论文回答这个问题,那是宏观的、全方位的研究;她从微观的、人物的心态、命运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去探讨。或许终一生之力也得不到正确的、完满的答案,她也认了。写长篇历史小说,是凌力进入探讨的一个途径。
多数初学者往往要经过短篇、中篇的训练才开始长篇创作,而凌力的处女作《星星草》,一出手就是上、下两册八十多万字的大长篇。这大概缘自她的多种学识、个人素养以及宏大的文学胸怀和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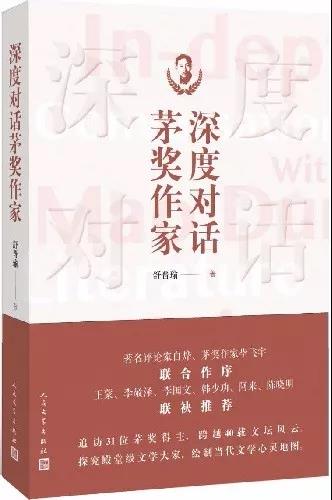
舒晋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舒晋瑜:您最早是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个多次进出导弹驱逐舰,进行导弹发射遥测的尖端武器科研人员,放弃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有点不可思议。能否回忆下您当年走上文学之路的情景?
凌 力:我选择通信专业,是遵从父命。是历史和生活把我逼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参加工作不久,十年动乱突然开始,亿万人民遭到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这使我陷入极大的痛苦、矛盾和忧愤之中。我没有去打“派仗”。我觉得党和人民养育了我,不管处于怎样的逆境,我总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还叮嘱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于是,我下决心研究一下历史。
在读史的过程中,捻军的英雄史实深深感动了我。太平天国后期,捻军处于中国革命大潮低落的逆境里,不后退、不投降,“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坚持抗争到底。在他们身上,我当时忧郁愤懑的心情得到了寄托。“四人帮”横行时,不允许我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我只好借助于捻军将士的英灵,借助于捻军苦斗的历史,来歌颂已经长眠于地下和仍在人间坚持战斗的人民英雄们。捻军在太平天国覆灭的逆境中奋起抗清,不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吗?陷于动乱的中国不会停滞不前,犹如当年的中国不曾停滞一样。这就是我写《星星草》的起因。
舒晋瑜: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能说说是有什么机缘吗?
凌 力:《星星草》差不多写了十年,先后改了七次。在投给出版社之前,我把这部作品送给戴逸先生,他从史学角度肯定了这部作品,并表示可以接纳我为清史研究人员。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很善解人意,同意我调出,我从此进入清史研究部门,并得到了主要从事创作反映清代生活的文学作品的许可。
舒晋瑜:一上手就是历史长篇小说,驾驭起来有难度吗?
凌 力:我喜欢长篇,是因为它能提供足够的容量来完成必要的积累,使作品达到真实可信,首先说服和感动作者本人。看一些作品,常有不满足感,因为人物的行动、感情根据不足,往往不到火候而硬写,就不能动人,看过也就忘记了。那时候,“要写出不同性格的人”,这一点是知道的。但是把写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精神灵魂的人放到创作的中心地位,就没有这样的觉悟了。倒是用极大精力铺写战争场面和历史悲剧的过程。而且受那时写英雄“高大全”的创作方法的影响,主要人物捻军领袖赖文光、张宗禹等人就显得理想色彩太浓而不可信,对捻军的最后失败提供不出充分的根据,致使这场历史大悲剧因此不够分量而失色许多。
舒晋瑜:但是这部作品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非常成功。
凌 力:有意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星星草》里的反面角色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反而显得比较活、比较真,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认可。其实,直到《星星草》的第四稿,曾、左、李的形象还跟“文革”中的反面人物差不多,极尽丑化之能事的。戴逸先生看过此稿后,提出:曾、左、李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用漫画手法去描绘,就简单化了,而且也不真实。接受戴老师的意见,重新查阅史籍资料,重新写过。当时只想再现这些人作为清代名臣、理学大师和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多重身份,在气质、谈吐、性格和风度上尽量向史实靠近。有些历史人物之所以反动,并不都是因为个人品质恶劣,更不会都是外形丑陋、猥琐不堪的。他们是因为代表着反动阶级,逆社会历史潮流而动,才在历史上处于反动的地位。无论就思想内容或是审美境界而言,《少年天子》都标志了新时期历史小说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也是堪称第一流的精品力作。
舒晋瑜:《少年天子》的创作起因是什么?
凌 力:《星星草》出版后,不少评论界老师在研讨会及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凡能听到、见到的,都认真聆听拜读,认真思索。虽然在意义、结构、形象、情节乃至文字等方面颇多受益,但最令我震撼的是这句话——文学是人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有滋味,越想越能从中悟出更多创作理念。其实我已调入人大清史研究所,正在比较系统地研读清代历史,很快顺治帝这个人物让我产生强烈的感应。一来觉得历来对他评价不公平,不是当他为庸主无所作为,就是拿董鄂妃说事儿骂他荒淫。翻案文章很吸引人,更吸引我使我欲罢不能的,是这个人独特的性格命运,跌宕起落的情感经历,以及通过他能映照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要试着把写人放在第一位!还未下笔,我就想好了书名——“少年天子”。

一部描绘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的长篇历史小说
舒晋瑜:创作过程顺利吗?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凌 力:《少年天子》的创作,得益于历史上顺治皇帝那起落跌宕、大喜大悲的特殊经历和特殊命运。写康熙皇帝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还是要围绕着写人,却不得不另辟蹊径。
舒晋瑜:《少年天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多家电视台热播,其编剧是作家刘恒。您如何评价他改编的“少年天子”?
凌 力:电视剧的前半部完全是刘恒的再度创作,比小说开始时的时间往前延伸了四年,从皇后进宫开始。小说开始时皇后已经废了,是第二个皇后进宫。我比较认可前二十集,因为第一,它是尊重历史的。我认为历史文学不是写史实,而是写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刘恒的创作写的就是可能发生的事,符合我所认同的历史文学的创作规律。第二,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关系方面都是尊重原作的,整个电视剧和原小说的创作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舒晋瑜:《少年天子》强调了封建社会的冷酷,一直冷酷到母子、夫妻之间,强调人性和政治制度间特别尖锐的冲突。您在处理这种冲突时是用唯美的手段,而刘恒却是用尖锐的手段。
凌 力:我很赞赏刘恒从真实的人性的角度去写。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像明朝永乐帝对反对过他的建文帝的臣子就特别残酷,放在油锅里炸,割舌头。对拒绝为他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诛十族,寻常的九族之外,还加上学生一族。把反对他的臣子的妻子、女儿、儿媳发往教坊。被糟蹋死后,钦命拖出去喂狗。可永乐帝在五次亲征蒙古时,又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在写清朝的各个皇帝时,要考虑怎么去认识他们的多面性。现在写康、雍、乾的视角比较单一,多是歌颂,把乾隆写成十全老人。修编《四库全书》,他毁掉了多少传统文化的好东西,这些却都没写。
在《暮鼓晨钟》里,我就侧重表现所有人性美好的东西怎么一步步被政治斗争抹杀掉,包括友情、爱情、善良……皇位一次次受到威胁,要保住皇位,就要整很多人。每个案件都要死人,每次死人皇帝本人都要失去一些东西。康熙是按孝庄的要求做一个好皇帝,但他内心美好的东西就牺牲掉了。
舒晋瑜:《少年天子》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凌 力:茅盾文学奖对于我,完全意外。那天一大早,人民日报社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我得奖了,我还以为是开玩笑,不相信。第一届《星星草》曾入围,那时我高兴、兴奋,觉得自己还真不错呢!后来落选,难免失望。但是,看到获奖者都是我敬仰的老作家、大名家,才感到自己怎么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又认真读了前几届中部分的获奖作品,相形之下,在深度、厚度以及艺术价值等等方面,差距太多太大。所以,此届《少年天子》虽入围,也就没太在意,因为不作此想了。却偏偏得了,实在没想到!
舒晋瑜:关于当时参评的具体状况,您了解多少?这部作品获得茅奖有争议吗?
凌 力:后来又听小道传说,因左右两派评委意见争执不下,《少年天子》属渔人得利。不知可属实?无论如何,我都没啥可自豪自傲的啦!
舒晋瑜:相对而言,您的很多作品比较受评论界的关注,如《少年天子》《梦断关河》等,评论家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您如何看待评论?
凌 力:文学理论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是严密的科学。我永远从事不了文艺评论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终生难望其项背。创作与评论,是相辅相成的,但又绝不相同,在看了很多评论家的文章后,我更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食品厂拿麦粉制成了漂亮的大蛋糕;食品检验所则将蛋糕分剖解析,化验出它的组成成分,指出哪些是必要的、合理的、有益的好东西,哪些是多余的、有害的甚至含有毒素的成分,以决定合格还是不合格,是伪劣产品还是优质产品。这对食品厂、对广大顾客,实在都是非常必要、非常好的事情。
这也是我理解中的创作与评论。创作是在合成:加工素材,结构人物和情节,大量渗入作者自身的思想观念、感情气质、艺术感觉、表达能力、文字技巧等等,最终形成了作品。而评论是在解析:分解提炼出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艺术特色、写作技巧,进而深入到作品人物乃至作者本人的心态意识等等精神世界里去进行更高层次的探讨。
创作凭的是直感、情感、灵感,在形象思维的范畴内驰骋。任何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一个作者。评论却真正遵循着科学的三严:严格、严密、严肃,是完全的逻辑思维。这确是智者才能胜任、令人肃然起敬的工作。我作为一个作者,作品和创作能够得到这样具有深度和广度、认真又诚挚的评论和理解,是很幸运的,弥足珍贵。
舒晋瑜:这些评论文章对您的创作会产生影响吗?
凌 力:通常,创作者比较盲目,也比较自信,不大听得进评论的说长道短。除了自满或脆弱之类的心理障碍之外,主要还是不能领悟。
我谈不到领悟,但多少开了点窍。《星星草》成书后,出版社请一些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座谈,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集中到两点:一是下卷的结构出现了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笔墨分散,影响了整体的艺术效果;二是正面人物不如反面人物成功。因此在写《少年天子》时就得吸取教训,在这两点上花工夫下力气,特别注意挖掘人物的感情和心态。随着创作的展开,也就渐渐开始领悟,一切都要围绕写人这个中心,这是法则。我自己也从这样的创作中感受到极大的乐趣。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凌力引以自慰的,是作品中的大多数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少数事件虽是虚构和想象,也是可能发生的。至于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和表现方法,就是她自己选择的角度了。
舒晋瑜:多年的创作,您大概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能谈谈吗?
凌 力:我不反对各种角度、各种方式表现历史的作品,它们各有自身的价值。我只是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历史小说要写的是所截取的那段历史中可能存在的人和事。首先是史料,记载着历史的真实,这是基础,是不能逾的“矩”;其次是推理,因为史料也有真伪,有不敢记或记不全的,经分析和推理,那些可能发生的,也是优质素材;第三个层次是想象,提供了虚构情节表现人物的巨大空间。想象,要靠大量的细节来支撑,而所有的细节都要遵循历史的可能性而不能生造。我这一类的历史小说作者,都会下大力气搜集、整理、阅读、研究大量的相关史料,为的就是写出真正的、浑然一体的历史小说。
舒晋瑜:您认为怎样的历史小说才是好小说?
凌 力:我希望所写的历史小说,能站在历史和文学之间,能成为边缘科学的一部分。历史学专家,往往对历史小说特别是历史影视作品有颇多微词,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历史文学作者的史学基础往往不够深厚,常会造成一些失误,甚至出某些笑话;另一方面,眼下的史学著作又越来越走向史论,离最早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之路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远。那么“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注定要消亡吗?
事实上在国外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以《史记》笔法写历史的史学著作,撰史者使用了历史尘埃落定后的、当代所具备的、大量的、各方面的丰富材料,尽量客观全面地用文学手段描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但受到学术界的赞赏,更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也可说是历史与文学间边缘科学的一部分,不过它的立足点在历史一边,而历史小说则须把脚步稍微移过来,更偏重于文学。我同意这样一句有总结意味的话:历史著作要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而历史小说要写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一切。
舒晋瑜:写历史小说,对您来说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凌 力:历史小说要遵循所有小说的艺术规律,比如要有生动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要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等等,但其最主要的特殊处,在于它必须具备的历史感,小说是不是真实可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然而,就创作的角度讲,这正是一个难点。最困难的,是营造特有的时代氛围,一位当代作者写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故事,使自己和读者都相信写的确实是那个历史时期,那就非得造足这种氛围不可。
写历史小说营造时代氛围,其实也就是在创造作品的神韵。这就需要多方面综合而成,难度相当大。比如,写唐朝,能不能使读者确信这真是唐朝,而非两汉、非两晋、非明朝?同样是写清朝,能不能写出清初、清中期和晚清的不同气氛和味道?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在营造特殊历史氛围上多下些功夫。
舒晋瑜:能具体谈谈您是怎么做的吗?
凌 力: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情况,力求在大的形势上不出格;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了解当时的民风、民俗、礼仪、制度、服饰、玩好等等,力争在自己心中有一幅当时的风情画卷,有一种那个时代的感觉,使自己能够形成一种判断力,在选择人物、情节或道具时不至于出大错。
舒晋瑜:您的历史小说,有散文的意境,因此有评论称您的小说是艺术品。在语言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凌 力:语言特别重要,常常会因为错用了一个现代词汇而破坏了苦心营造的整个历史氛围,所以需要特别小心。在写清代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我掌握的原则是决不让现代语汇出现在古人口中。
舒晋瑜:那么,您判断古人说话的语言根据来自哪里?
凌 力:一来自清代剧本,如《缀白裘》一类在清代流行的演出本;二来自清代白话小说,从顺治年到清末各朝都不少;三来自清代案卷,审案录供中有大量的常用语言、生活语言。
舒晋瑜:您的小说创作,善于选材,也长于虚构和想象,同时您又尊重史实。如何在虚构和史实间找到合理的平衡是否对作家来说也是很大考验?能具体说说吗?您如何看待史实和虚构的争论?
凌 力:在虚构人物情节时,没有史实做支撑,营造历史氛围就特别困难。我在《暮鼓晨钟》一书中写康熙帝幼年的那一段,宫廷外朝廷上的一系列大冤狱都是史实,而宫廷内小皇帝的生活则是虚构。初稿出来后,我觉得后者有两大不足,一是感觉不到清初宫闱的特点;二是太皇太后过于英明,料事如神得没有来由。而这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补足。后来看到一则史料,说:清宫找到明宫遗留下来的几大箱小脚女鞋,全都镶珠嵌玉十分华丽精致,满族妇女都是天足不能穿,扔在那儿又可惜,就把鞋上的珠玉拆下来,镶嵌在新做的绣花鞋上,供宫妃宫眷们穿用。当时风俗,小辈妇女为长辈上寿时,有做鞋为礼的习惯。根据这两点,我虚构了小康熙发现祖母(即太皇太后)的贴身侍女用拆珠玉做绣鞋为手段传递情报这个情节,用来照顾好几方面:一是太皇太后有情报网服务,明察善断就有了根据;二是小康熙受祖母统治术的影响,日后他建立特别的耳目监视官员,即后人称之为使用特务的行为有了来历;三是营造出由明入清、由汉人统治变为满人统治的宫闱中的特殊氛围;四是表现出宫中用度节俭的清初的特点。这样去弥补初稿中的缺憾,作品的历史感就增强了,清初宫廷的意味也浓了很多。
对于史实和虚构的争论,每位作者和读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都有它的道理,孰是孰非,彼此平等,何必强求一致?
舒晋瑜:在创作中是否也有些弥补不了的缺憾?
凌 力:是,有些始终想不出好办法弥补。比如写历史大背景真实、人物虚构的历史小说行不行?甚至背景和人物全都虚构行不行?尽管我弄不清这样写算不算历史小说,就按照历史小说的规律去写行不行?但不论怎么写法,只要写的是历史文学,就要力争写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充满历史韵味的作品来。当然,让今人穿上古装在作品中表演各种悲喜剧,或让唐宋元明清朝的古人在银幕荧屏上幽默地说几句现代语汇,作者自有他的奇思妙想,所谓各有各的高招,不能一概而论。
舒晋瑜: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您认为选材有何特殊要求?
凌 力: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历史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作者选择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动的,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
之所以取材于历史,是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是真实存在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丰富事变、事件,不是任何一个天才头脑能够完全设想出来的。事变、事件既然发生,那就必定有发生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等合理的根据,作者自己首先就要确认其真实性,而不要像读传奇小说时产生“瞎编”一类评语和受骗上当感。
同样的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认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是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史料,也带有著作者个人爱憎好恶的色彩,真正的董狐直笔几乎是没有的。现存的史书史料相较真实的历史而言,肯定是不完全的,这倒给历史小说作者的推理、想象提供了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
舒晋瑜:在《星星草》中歌颂农民起义,在《少年天子》里又歌颂有作为的帝王,矛盾吗?
凌 力:我写历史小说,不只在介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不为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说到头,仍旧回到文学的功能这个初始命题上来了:总是想表现和颂扬那些使人类奋发上进的精神品质,颂扬过去、现在、将来都被人们追寻的真善美。《星星草》写的是英雄的失败和失败的英雄,颂扬逆境中人类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少年天子》写的是封建君主的悲剧命运,若说歌颂的话,是在歌颂有所作为的开创精神和真挚的情爱。当然,农民和地主、平民和皇帝以及一切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由许多社会科学门类专门研究,全面分析。以表现人为主题的小说,只能通过个性反映共性,努力使之能为当代人和后代乃至下个世纪的人类关心、理解和接受。
写作之余,凌力喜欢京剧,喜欢动画片。她在不同的艺术各类中都能获得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荀慧生演红娘,他当时已经发福,有人笑称“娜塔莎大婶”,可是看着看着,观众就被他们带进特定的《西厢记》的环境,忘却了形貌和年龄上的不合。她说,今人写历史小说本有形似的有利条件,如果能达到神似的境界,照样能够产生令人信服的艺术效果。
舒晋瑜:听说您喜欢看动画片,是否从中获取了有益的营养?
凌 力:我自小爱看动画片,看得多了,就产生问题,产生疑惑。我国的动画片,从最早的《谢谢小花猫》到《大闹天宫》《神笔马良》《人参娃娃》《哪吒闹海》,及至近日的《好猫咪咪》《黑猫警长》等等,无不爱憎分明、是非清楚、正气凛然,好人绝对好,坏蛋一定坏。可是看外国的动画片,如《汤姆与杰瑞》,猫和老鼠很难说谁好谁坏,都干过坏事,也都做过好事;都欺负过人,也都帮助过人。有时剑拔弩张,有时又充满温暖的人情味儿。就连被芭蕾舞剧描绘成绝对凶残可怕的恶魔,在动画片《天鹅湖》中也因爱上奥杰塔公主不能自拔而痛苦万分。这些对吗?我不知道。但似乎这样的动画片更为孩子们所喜爱,也更能令成年人唇边浮上会心的微笑。是不是因为它更加真实因而就更加亲切呢?是艺术的魅力还是人性的光辉?
我觉得,作者写他的人物,不仅要冷静,而且要有博大胸怀,同等地对待他的真善美和他的假恶丑。须知他的真善美和他的假恶丑并非与生俱来,并非凭空生发,是后天的社会生活塑造形成的。作者写的是人物,表现的则是形成人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我想,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1987年至1992年,凌力为了创作康熙系列小说,先后去了新疆、云南、湖南等地考察。在昆明,她去了吴三桂绞死南明永历帝的旧址。在新疆,她颠簸天山南北,写出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篇《失落在龟兹古道的爱》和短篇《追寻成吉思汗的后代》。
舒晋瑜:在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情、深情,为所钟爱的人奉献一切,男性形象都具有英雄主义的光彩,能说说您是如何设置您笔下的人物吗?在再现和表现历史生活、历史人物上,您是怎样做的?
凌 力: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我每写一部长篇小说,除去占有和消化大量文字资料外,都要去实地考察,印证史料,获得感性印象。
舒晋瑜:《北方佳人》的创作,最初是怎样的想法?
凌 力:最初设想,《北方佳人》以清初草创开国为背景,表现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姐妹姑侄为代表的满蒙杰出女性,也是长篇历史小说系列“百年辉煌”中按时序的第一部——当时已经完成了《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时逢香港回归、百年雪耻,研究历史的人不能无动于衷,另外开篇以写鸦片战争为背景的《梦断关河》,也了却我多年来探究梨园这中国特有社会阶层的心愿。五年后再回头拾起旧题目,情况已经不同,有关清初人物事件的作品大量涌现:电影电视戏剧、小说传记秘史,真实的历史和人物被淹没了。既没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和能力,也没有凑热闹的兴趣,在追溯孝庄家族源流时遭遇北元历史,萨木儿和洪高娃从历史尘雾中款款走来,把我抓住了,抓得很紧,直到两年前定稿。她们取代布木布泰,成为了《北方佳人》的主角。
舒晋瑜:驾驭这样大的题材,展示清代帝后将相的小说,对您来说是否游刃有余?
凌 力: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把“雄浑”置于第一,品评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数十年写历史小说,很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它太高了,终一生之力,也难以达到。
本想在日后创作中努力提高一把的,却得了场不能劳累的富贵病;原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可花,转瞬间已年近古稀;原先白纸黑字应许要完成的“百年辉煌”,看来也办不到了……但人生哪能没有遗憾?写不了大部头可以写小文章,就算小文章也写不成了,也还有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支持我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 选自 舒晋瑜《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