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是一座活的诗歌博物馆。”每一次见吴思敬,我都忍不住这样感慨。他知道那么多诗坛的掌故,了解那么多诗人的细节,诗歌史上大小事件了如指掌!采访时谈到公刘,他脱口背出《上海夜歌》;谈到顾城,他少年时写下的《星月的由来》又信手拈来。他对于诗文的博闻强记,对于诗人们亲切又不失冷静思辨的体察,对于诗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及时梳理并做出准确严密的判断和总结……

吴思敬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吴思敬不仅仅是一个在场者、见证者、书写者,更因为他广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为推动诗歌发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成为中国诗坛不可替代的人物。既有对中国新诗宏观的、整体性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梳理,重要的如《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20世纪新诗思潮述评》等,也有对诗坛现象的剖析以及诗人和诗歌文本的翔实、深入、准确、独到的个案研究。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后所面临的冷落、边缘与尴尬,甚至到了近十年来物欲和现代化进程空前加速的过程中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吴思敬仍然以个性化的方式深入了诗歌历史和繁杂的诗歌现场当中,尤其是对1980年代以来复杂的多元诗歌格局和驳杂的诗歌现象予以独到而精准的追踪、考察、分析和反思,确立了一个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系统、完整的话语谱系。在青年评论家霍俊明的眼中,“吴思敬除了深入诗歌理论的系统建构之外,同时站在每一个时代的高坡上,从而能够看清一个时代的诗歌迷津与真实面貌,而他不断在诗歌现场的介入、观察和感同身受也使得他能够更为真切地体会到诗坛的冷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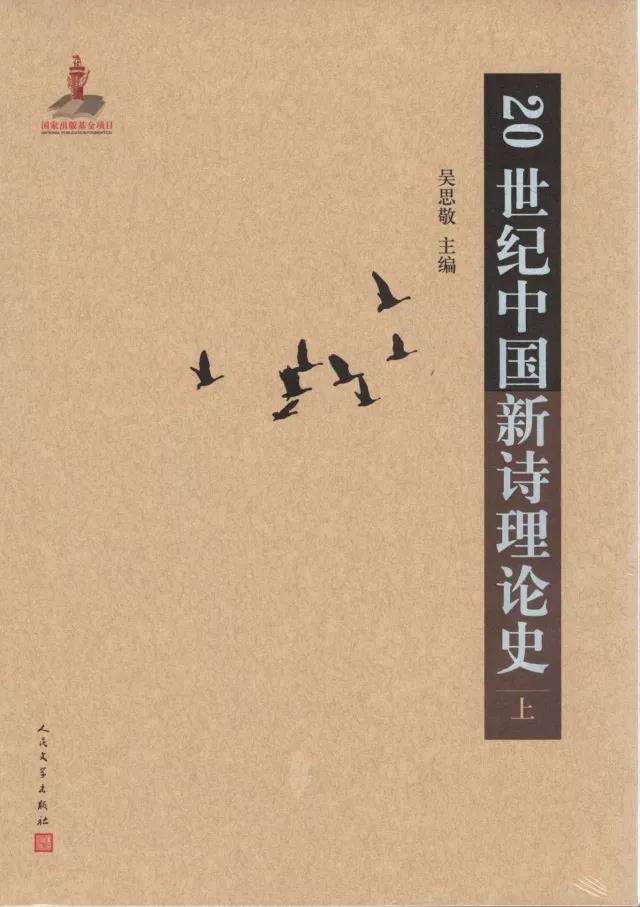
我与顾城
中华读书报:今年是顾城去世25周年。您曾经为顾城写过最早的评论,顾城去世之后您写了《〈英儿〉与顾城之死》,并在《诗探索》上编发了关于顾城的专栏。能说说对顾城的印象吗?
吴思敬:顾城是1993年10月8日离世的。一晃,25年过去了,顾城之死引起的惋惜、争议、漫骂、谴责都已化作泡沫,留下来的只有他的诗。
我最初见到的顾城,不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白净的皮肤,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大孩子。外在的温和与内在的反叛,现实生活的压力与内心的童话世界,在他身上不断纠结、碰撞,构成了他独特的心灵世界。许多诗人的作品可以复制、模仿,顾城却是不可复制,很难模仿的。因为他那极其独特的气质、个性和语言方式,只是属于顾城自己的。在朦胧诗论争中,顾城一直是个焦点人物,当时他对“做螺丝钉”的反思,他的《小诗六首》,还有他写嘉陵江“展开了暗黄色的尸布”等,引发了批评。出于对顾城独特价值的确认,也是为了对正在挨批的诗人予以道义上的支持,我决定给顾城写一篇文章,对他的创作做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为此,我去万寿路总后大院顾城家里采访了他的父亲顾工和母亲胡惠玲,了解了他的成长过程,以及许多他的不可思议的趣事。比如剥毛豆,有黄的有绿的,他会分成两拔,命名为黄军团、绿军团,让它们“打仗”——那是他二十多岁的事情了。顾城小时候曾经在窗台上摔到地上导致脑震荡,后来总会产生幻觉。我通过采访顾城了解了他内心深处,他外在表现温和,一旦情绪爆发就无法控制,他的心理是有特殊问题的。
顾城是一个怀有孩子一般梦想的诗人,是一个怀着纯净的心灵看待世界的诗人,具有独特的气质,感觉敏锐而纤细。顾城的较为成功之作,都是基于感觉,但又不只停留在感觉上,而是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表现了一些现实和理想世界矛盾的情景。他12岁写出《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他15岁写出代表作《生命幻想曲》:“……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写世界与自我的融合,显示了超拔的想象力,既是十几岁少年的感受,又不是十几岁的少年都能写出来的。
当然也应看到,顾城的某些作品,还只是停留于一瞬间直觉、幻觉的捕捉,其中虽不乏新鲜的意象和诗意的萌动,总的说来,基本上还只是感觉的记录。顾城自己是把这类作品叫作“心理笔记”和“意象笔记”的。这种“笔记”中某些章句虽然发表了,但严格说来,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有的作品被人诟病,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尽管顾城的诗存在一些缺陷,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顾城是一个完全自闭和沉溺于狭小的心灵世界的诗人,顾城的诗歌中同样有对祖国、人民和现实的关注。顾城是一个丰富的有多个写作向度的诗人,不是“童话诗人”这一称呼所能完全定型与概括的。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写出《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谈顾城的诗》。
中华读书报:1993年顾城的悲剧发生后,您做了很多事情。
吴思敬:记得顾城悲剧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京西八大处北京军区招待所开“新诗潮研讨会”。当时《诗探索》正在酝酿复刊,我当机立断,现场组稿,请与会的诗人、顾城生前好友文昕撰写了很有史料价值的《最后的顾城》,请与会的诗评家唐晓渡写出深度解析这一悲剧事件的《顾城之死》,还请顾城幼儿园时代的朋友姜娜撰写了《顾城谢烨寻求静川》,此外还收集了《顾城谢烨书信选》,组成“关于顾城”这一专栏,在《诗探索》复刊后的1994年第1期上推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进一步研究顾城其人其诗,提供了最早也较为可靠的材料。顾城出事后,《文艺争鸣》的张未民打电话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英儿〉与顾城之死》,从顾城“天国花园”的幻灭及顾城的心理缺陷等方面分析了顾城之死的原因,并讨论了顾城的后期作品。顾城是我关注比较多、关系比较好的诗人,我上世纪80年代住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的时候,他曾来我家多次。1986年5月诗集《黑眼睛》出版,他亲自送来一册,扉页上题写着“人,类也——敬请吴思敬老师指教”,就是说我与他是一类人、以类相聚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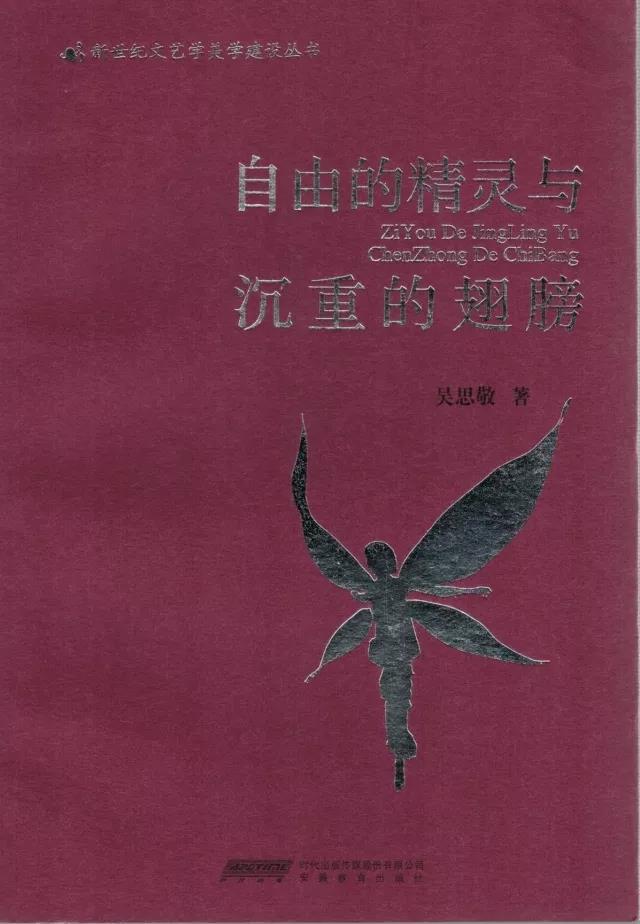
朦胧诗论争
中华读书报:谢冕曾经说过,您是支持朦胧诗的“一员大将”,孙绍振对您在定福庄会议上“言必有据,说着说着就掏出一张卡片”印象深刻,您曾参与朦胧诗论争,为朦胧诗做了很多工作。
吴思敬:1979年春天,朦胧诗人开始走进公开的刊物。当年的《诗刊》先后发表了《回答》《致橡树》等诗歌。激进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狂热地支持朦胧诗人,一些观念保守的人则猛烈地批评他们。朦胧诗论战的初期,当时还不叫“朦胧诗”,而是被叫作“晦涩诗”“古怪诗”。出于对朦胧诗人艺术创新的肯定和支持,我参加了论争,1980年7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意在为这些年轻人的诗呼吁一个生存空间。文章发表没几天,就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不同观点,同我“商榷”。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朦胧诗”这一带有戏谑色彩的名称才开始传开,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诗刊》认为有必要把不同观点的两派代表人物召集到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于是1980年10月在北京东郊定福庄的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召开了“诗歌理论座谈会”。
这次会议是在朦胧诗论争高潮中举行的,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代表人物都到场了。谢冕、孙绍振、我和钟文等是朦胧诗的坚定支持者,持批评态度的则有丁力、宋垒、李元洛、丁芒等。当时围绕朦胧诗的争论涉及到大我小我、自我表现、现代派的评价、诗与时代、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争得不可开交。孙绍振是个天生的演讲家,我和钟文是大学老师,在讲课中锻炼出来,我们辩论起来比较有优势。我平常就有积累卡片的习惯,发言提纲也写在卡片上,孙绍振说我发言中不时掏出一张卡片来,确实是那样。这个会的最大好处,是有一种自由争鸣的空气,会上争论很激烈,会下仍然很友好。
记得辽宁诗人阿红曾在晚上拉我到他的房间去做一种文字游戏,把许多词汇抄在麻将牌大小的纸片上,然后字朝下像洗牌一样地打乱,再随意地把纸片分排成几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像不像一首朦胧诗。阿红对朦胧诗是有批评的,他发起的这个游戏意在讽刺朦胧诗,无意中倒是开启了如今电脑写诗的先河了。我到现在还很怀念这次会议的会风,朱先树写的综述称之为“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大家畅所欲言,争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上纲上线,比较宽松。近些年来,这样气氛的诗歌会议很少见到了。
在定福庄诗会之前,我写了阐释朦胧诗美学特征的文章《说朦胧》(《星星诗刊》1981年第1期)。定福庄诗会之后,我把自己的发言稿做了整理,写成《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一文,集中表达了我对诗歌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发表在《诗探索》1981年第2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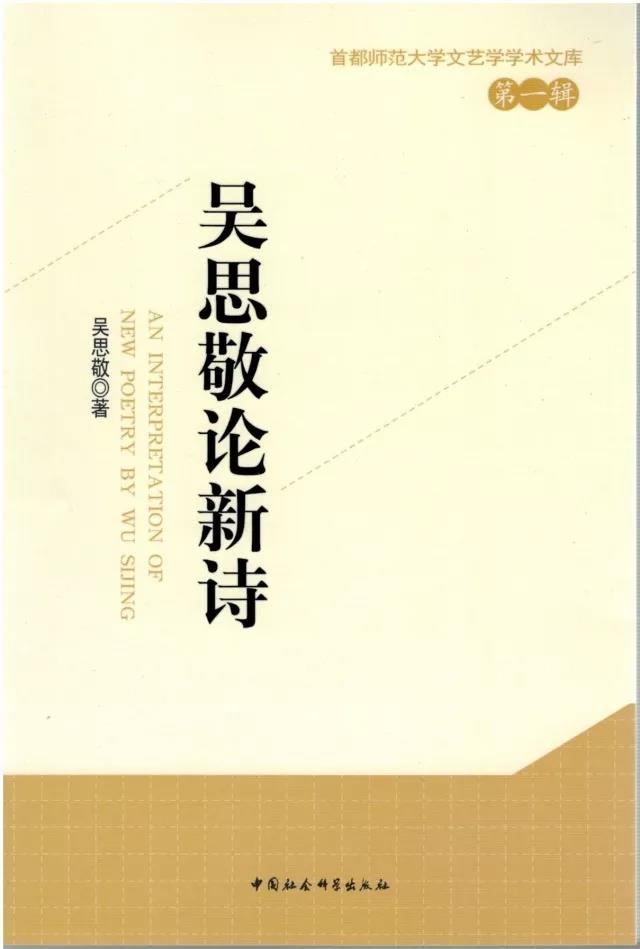
“盘峰论剑”
中华读书报:世纪末的“盘峰论剑”是一次重要的诗歌事件,能够折射出90年代诗歌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您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这次会议是怎样召开的?您认为“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化有什么内在的根源?
吴思敬:“盘峰论剑”是指1999年4月16—18日在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诗探索》编辑部策划并发起的。到了90年代,商业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包括某些官员,都在忙于经商、下海,没什么人再关心朦胧诗、“第三代诗”,先锋诗人的外在压力大大减轻了,而先锋诗人内部的矛盾倒开始凸显出来了。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与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显示了截然不同的编选思路与取舍原则。沈奇在刊登在《诗探索》1999年第1辑中的《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一文中敏锐地指出:“显然,一种新的分化正在这个阵营内部发生”。作为诗歌评论第一线的《诗探索》同仁,自然也感受到这种分化。我们想与其让不同意见的双方隔山打炮,何不让他们坐在一起面对面、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
我们发函把先锋诗人中不同观点的两派请到一起,一方是以王家新、西川、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方是以于坚、伊沙、杨克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还有陈仲义、程光炜、唐晓渡、陈超、沈奇等评论家。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中,一开始没有邀请徐江,是伊沙给我打电话,说徐江“最善于开会”,希望把他请来。这样我们又邀请了徐江。徐江果然能言善辩,成了民间写作的主要发言人。
中华读书报:听说这次会议中争论十分激烈,其中最尖锐、最有锋芒的观点是什么?您在这次会议中是持什么态度?
吴思敬:作为会议的主办单位,我们只是把对立的双方邀请到一起,充分交流意见,我们并不指望一次会议便能消除分歧,统一认识。谢冕老师在会议开幕时说:“交流就是目的,理解高于一切,依然不会有、也不试图有任何结论”。这也正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尽管我们事先估计到会有激烈的辩论,但会议开场后的剑拔弩张之势,还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在听到于坚、伊沙等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尖锐批评之后,王家新做了题为《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的发言,他拿着发言稿,声音都变了,手在发抖。而听不下去的于坚,则“砰”地一摔门,走出会场。我在现场,真有些紧张,生怕他们大动干戈。好在大家都还理智,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
我在会议的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会后,我把自己的观点写成《裂变与分化: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一文,发表在《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上。我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先锋诗歌界两种不同的写作趋向之间矛盾冲突的一次爆发。有人把盘峰诗会上的争吵归结为两派诗人的“争权夺利”,这是不全面的、也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两派诗人情绪激动的争吵的后面,确实有着学理的因素,有着不同的诗歌美学追求。就这两种写作的诗学主张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高度,追求超越现实与自我,表现为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就否定其存在价值。“民间写作”强调活力,强调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也不能因其夹杂若干草莽与粗鄙成分就轻易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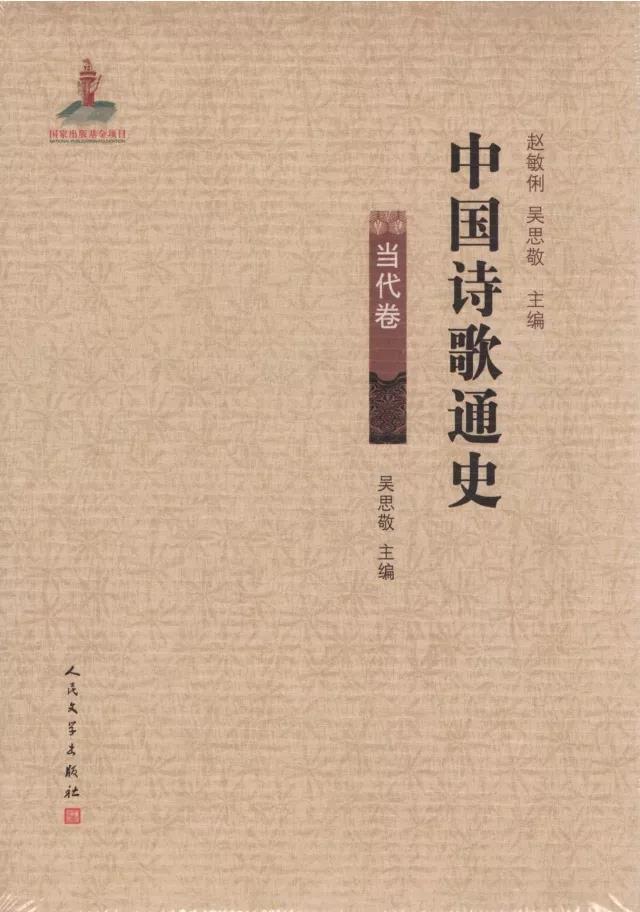
实际上,尽管两者有诗学观念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它们都各自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各有合理性,也各有局限,理应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盘峰诗会的争论尽管有些情绪化的成份,但毕竟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坦诚的对话。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诗的领域从来就不应是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正常的。盘峰诗会的争吵打破了诗坛的平静,两种写作方式的冲撞,一方面打破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也会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
中华读书报:20年之后如何看盘峰论剑?这次论争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吴思敬:盘峰诗会尽管论争激烈,充满火药味,但从这场论争的后果来看,倒是积极的,它为世纪之交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实际上诗人们通过不同观念的碰撞,经过反思,意识到以前写作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片面性,有助于他们改变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可能。盘峰论争挑开了先锋诗坛的内在矛盾,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对新世纪诗坛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论争过去之后,诗歌界出现了十多年相对平稳的局面。尽管后来发生的一些诗歌事件经过媒体炒作,喧嚣一时,但关乎全局的、在诗学层面上剑拔弩张式的争论并不多,当年的知识分子诗人在和民间写作诗人一起出席会议,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倒是常见现象了。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诗歌研究已经四十年,您愿意怎样总结这四十年历程?
吴思敬:1996年我在给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第一部著作《诗学:理论与批评》所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这是我当时心态的写照,现在时间又过去了22年,但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不管诗歌和诗歌评论滑向边缘的何处,我都甘愿当一名“边缘人”,坚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

